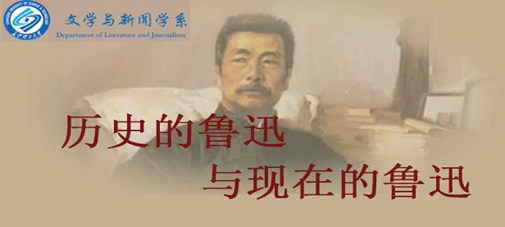


2020年9月15日晚七點半��,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��、博士生導師��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張福貴教授受長沙理工大學邀請��,通過騰訊會議進行了以“歷史的魯迅與現在的魯迅”為主題的學術講座��。講座由文新系易彬教授主持,來自文新系各級研究生、本科生、部分老師以及校外的人士,共計近150人參與了會議��。
從魯迅生前到魯迅死后��,我們對魯迅的評論從來沒有停息過��。作為中國的學生,我們從小就在教科書中讀到魯迅,但也許我們對魯迅的了解并不全面��。今天張福貴教授帶領我們走進歷史語境中��,在浮浮沉沉的歷史中去了解魯迅��。
張福貴教授以“歷史的魯迅”和“現在的魯迅”為講座的兩個切入關鍵點來向我們闡述從歷史到當下,人們對于魯迅的認識。魯迅是個富有極強批判精神的斗士��,魯迅生前“罵過”很多人��,但魯迅不僅會“罵人”��,也被別人“罵過”。處在“歷史”之中的魯迅��,從來不乏有對其批評和否定的聲音��。
首先是對于魯迅文學價值的否定��。早期,比如成仿吾對魯迅的文學作品的否定��,再后來更是有不少人質疑魯迅的文學創作能力��,因為魯迅沒有長篇小說面世��。“國學大師”劉文典更是寫文從魯迅的性格、人品到小說創作等方面指出魯迅的“十八宗罪”��。在張福貴教授看來��,對于魯迅文學價值的判斷是一種審美判斷��,宜用寬容的眼光來看待��。
其次是對于魯迅心理性格的否定��。魯迅激烈而尖刻,這是一種“斗士”的性格��。在歷史上��,比如陳源(陳西瀅)��、林語堂、蘇雪林等人都有對魯迅性格的批評��。對于一直為人所爭議的魯迅激烈而尖刻的心理性格問題��,張福貴教授認為需要正視��。在他看來,魯迅的尖刻來源于他的深刻��,魯迅的激烈來源于自信和決絕��。一個社會的改變��,一種思想的覺悟,往往是由于個人的先行覺醒��,當覺醒的個人面對未覺醒的大多人��,往往是激烈的��。當新生力量還不足以抗衡舊的龐大的陣營時候,他必須以這種“決絕”��、“激烈”的姿態去面對去反抗��,正如魯迅所言 :“勇者憤怒��,抽刃向更強者;怯者憤怒��,卻抽刃向更弱者��。”因而,這種“決絕”��、“激烈”的姿態是其實不得已而為之的。作為先行的覺醒者的魯迅��,他是激烈的��、尖刻的��,也是孤獨的、痛苦的��。
而在八十年代之后��,對魯迅最大的批判是對他人格的批判��,尤其是人們在朱安和魯迅這段封建婚姻中對魯迅行為的批評,張福貴教授則認為魯迅和朱安其實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��,也許魯迅在心理性格��、人格上有所缺陷��,但是“有缺點的戰士,畢竟還是戰士��,完美的蒼蠅��,終究不過是蒼蠅��。”當我們對歷史中的魯迅的闡釋��,應該帶著一種相對寬大的��、包容的態度去看待那些缺陷��。
而對于“現在的魯迅”這一命題,張教授認為在當下這個語境而言��,魯迅已不僅僅是周樹人��,而成為一種文化��、思想的符號,具有超越性��。張教授懇切地提出��,“要去讀魯迅的全集,讀完魯迅全集你會感慨,中國有魯迅,真是幸事,不僅是中國的,甚至是世界的”��、“在這樣一個紛紜復雜的世界里��,我們需要魯迅��。”
魯迅究竟何以偉大?張福貴教授認為��,魯迅其偉大就在于魯迅為我們民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命題��,其核心就是“要使非人成為真的人”��,要“改造國民性”。從魯迅的作品探去,我們會發現魯迅一直致力于構建全面��、完整的人性(即立人)��,魯迅意在根除民族的劣根性��,以達到對人性的關懷。這在魯迅筆下的眾多人物如阿Q、祥林嫂��、孔乙己等人身上我們都能有所察覺��。
張教授分享完畢后是同學們的發言提問環節��,大家都十分積極地提出了自己對魯迅相關問題的思考與疑問——“魯迅的生命止于1936年,那么魯迅如果生命不止于此,這樣一個斗士的他在之后可能會有怎樣的表現��?”��、“魯迅的鄉土文學創作很豐富��,為何在城市生活了很長時間后,他仍然站在鄉土文學的角度來創作,而不是都市文學��?魯迅在三十年代對左翼有著極大熱情��,但是他并沒有相應的左翼革命文學創作��,如何看待魯迅現實和創作的偏差?”、“請問一下老師��,您認為魯迅在那個教育普及度不高的時代��,對占中國絕大多數的普羅大眾有多少影響?最終挽救中國的是覺醒的知識分子還是懵懂的平民百姓呢?”……對于同學們的提問��,張福貴老師一一提出了客觀中肯而條理清晰的解答��。在這近兩個小時的學術分享中��,張福貴教授語言表達流暢��,思維嚴謹縝密,對于魯迅相關的材料信手拈來��,一氣呵成��,令在座的聽眾們對“熟悉又陌生”的魯迅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��。
講座最后,易彬教授進行了一番總結:“張老師對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非常熟悉,各類文獻都是信手拈來。盡管張老師一再強調對魯迅有著特別的情感��,但他對魯迅的評價始終保持著一個比較客觀的態度��,讓我們重溫了歷史魯迅的原貌��,也體味了今日魯迅的價值。張老師對于‘文學的魯迅’和‘現實的魯迅’,‘魯迅’和‘周樹人’的區分,都是有著意義的命題。借用張老師的著作《遠離魯迅讓我們變得平庸》的說法��,我們也可以說��,這一場講座��,也會讓我們在這樣一個庸常的時代,依然能保留思想的火種,依然可以不那么平庸,或者說��,可以延緩邁向庸常的步伐��?�!?/span>
(圖文/潘潘)